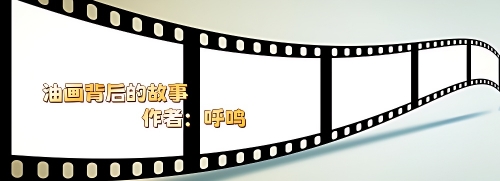
***(呼鸣《油画背后的故事》~连载中)***
112:电影《八女投江》的冰天雪地(二)

(左图:我和陈布谷(左一)是联合美工,合作的很默契投人。)
拍到冷云难产时,大雪纷飞,杨导望着天说:"好大雪啊!不用做效果了。"扮演冷云的凯丽,身上、帽子上、假发上都落满了雪,脸都冻紫了。打板开机了,几个抗联女战士为冷云接生,我抱着死婴,让战士事先往铝盆中倒了一暖壺的开水,等水还有热气时,我把手里的死婴放在温水里,刚刚放进去不久,沈华芬就对我说:"呼鸣,死婴准备!"画面上一双手托着冒着热气的死婴递给了冷云:"孩子,她,她不行了"……冷云撕心裂肺的哭声回荡在山谷。
我把蓝包袱皮严严实实地裏好了死婴,又放回大铝盆对小张说:"拿上铁锹,深埋了吧。"小张问:"不留着下次用吗?"我突然明白小张并不知道这是真的死婴,以为是道具组的模型。"我说:"你就当是真人埋了吧,记住深埋!"大雪中,摄制组的人们都趟着没膝的雪坚难地行走着,我见小张一手拿着食堂的大铝盆,一手提着空暖壺赶了过来,我问他:"那具死婴你们埋在哪了?"另一个小战士扛着铁锹,指了指一棵倒在不远处地上倒着的大树说:"那边,放心吧呼老师,就把她埋到那边了。"
我们仨人最后上了车,演员们七嘴八舌地说:"呼鸣啊,真有你的,女婴做得可真像啊!是啊,奥斯卡给你最佳道具奖了"……这事只有制片主任知道真情,马上大声说:"安静!大家都眯一会儿,保存实力,一会儿下车还要继续拍摄呢!"雪越下越大⋯⋯

(右图:电影《八女投江》抗联战士的剧照。)
春天在雪没有完全溶化时就悄然来到了小北湖。冰河断开的世界又开始了流动,玉树斜过碧空。解冻的湖水清澈见底。我们在湖边拍了一场全剧最轻松的戏。抗联女战士在战利品中找到了一面小镜子,女战士们轮流地照,小小的情节流露出女战士爱美的天性。由于找群众演员很困难,组里凡是女的几乎全扮上了抗联女战士。我也是其中的一名群众演员。
我们再一次进夹皮沟的山里也是个大晴天,那个拍摄现场也就是两个月前拍冷云大雪生产的同一个现场地。好像是拍最小的抗联战士王惠民和她父亲相见的那场戏。雪溶化得很松软了,但仍然不见地面裸露。在车上杨导和主创人员(导、摄、美)说着这场戏的画面,什么360度的旋转,蓝天白云,春天的树梢……

(左图:那天的拍摄真把我们累着了,为了拍摄这场大雪,大家几乎是24小时没睡,许多人都是象我这样,索性躺在雪地里小睡……)
我踩着雪走,是为了听那咯吱咯吱地踩雪声。所以和大队平行地走着,突然眼前一个颜色使我止住了脚步。白雪中露出了一角蓝印花布,天啊!这不是我给那具死婴裏身体的蓝印花布吗?怎么会? 我上前一看彻底呆了。我几乎要坍塌,摇摇欲坠。一张已经泡涨变形的死婴脸空空地敞在那里。身子却还埋在雪里,我什么也没有想,摘下帽子装满了几帽子的雪,连泥水和枯叶子一起,连忙盖上了那张裸露的小脸,生怕她会睁开眼看着我……
我象是丢了魂似的拍完了这场戏。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里那张变型的小脸常常来到我的梦乡。我总觉得我对不起她的,真的。为什么非要用她当道具?为什么不能说服导演等上十几天,等厂里寄婴儿模型来?为什么我没有和小张他们一起掩埋她?又为什么我没有检查,发现她并非被深埋……
在《八女投江》的拍摄接近尾声时,天真的变暖了,终于到了可以拍摄最后一场戏:八女投江了。各个部门都紧张地准备,其实大家也都想家了,出来外景地算算快四个月了。就在拍摄的前一天,沈华芬副导演问了摄制组里的每个女性工作人员,问谁会游泳?因为扮演郭桂琴的演员来例假了,不方便下凉水了,需要一个背影替身。当她问到我时,我说没问题,我会游泳,就这样,化妆组的陈倚红,给我剪了个和演员郭桂琴一模一样的短头发,服装组的李秀荣给我找来一身和郭桂琴一样的服装,第二天我和其它七女一步步走向了水的深处。我还记得那水啊,真够凉的……

(我们全力以赴地拍摄最后一场戏:八女投江……)
113:《白日梦》终于醒了

(右图:怀念八十年代的春天)
1986年6月,我写的儿童科幻电影剧本《白日梦》发表在《八一电影》杂志上了。文学部的赵俊仿主任非常肯定这个剧本。由鲍老师负责这个本子的修改,由于八一厂是部队电影厂拍部儿童片几乎是不可能。后来经人介绍,我拿着这个剧本找到了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罗小玲导演。罗导也非常喜欢这个本子,当即请儿影文学部的张老师(五十年代影星张圆之女)做这个剧本的文学编辑。罗晓玲导演,是四十年代影星黎丽丽的女儿,罗导来自电影世家,她对电影语言非常敏感,和她的每次对话,都使我离电影艺术又进了一步,学到了许用电影语言来塑造人物。她对《白日梦》的肯定更使我信心大增。她转告我,于兰厂长也认为,《白日梦》是建国以来很有新创意的,发人深醒的儿童科幻影片。
那段时间里我也去过北京景山少年宫考察模型飞机,热汽球等能否在影片中运用的可能性。同时我又重新考虑是否可以尝试动画与真人结合拍摄等等的技术问题,当时只要我一有时间就去黄亭子儿影厂宿舍找罗导讨论修改剧本。后来我终于把《白日梦》变成真人与动画与特技多种表现手法的儿童片,比如:小凡上学从他家六层的窗户,就可以伸出滑梯滑下,在公交车堵车时,车子可以腾飞前行。中国传统飞人设想和热气球的能量设想在片子中通过小凡的想象也都有体现,当时我常常陶醉于不着边际的设计中,好玩极了……

(左图:《白日梦》在1986年发表后,我又改了第三稿)
说心里话八十年代上演的所有电影对我来说非常肤浅,都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多数的电影甚至不如文革前的黑白电影的手法纯粹和朴实。就是能看的电影也是少得可怜。有一天,我和邵飞到东单大街的著名的大华影院,想去看一场国产恐怖片。片名好像是雾都什么什么,电影广告上写着“儿童不宜”。就这四个字,足已让我浮想联翩。电影开始后,影片的故事情节根本就谈不上恐怖,全靠音乐渲染气氛了,音乐还真不含糊,从头到尾地响着,最要命的是潜入敌人心脏的我党特工,牺牲前又开始从上衣口袋里摸红布包,左一层、右一层地揭着,颤颤抖抖地拿出几块大洋断断续续地说:“这,这是我的党费。”画面又旋转着出现了青松、白云……。电影院的灯全亮了,我们沮丧地拥在出场的人群中,邵飞不紧不慢地拍着我的肩说:“这片子不仅是儿童不宜,成人也不宜。”说完我们大笑不止。

(右图:这是罗小玲导演(左三)和丈夫马力(左一),女儿绵绵(左二)的合影)
那会儿在民间也是真够热闹的。人们打完鸡血,喝过红茶菌。一下子身边出现了许多有特异功能的大仙儿,测字的、嗅出香味的、能发功治病的、能遥测破案的、开天眼的、灵魂出窍的,意念移物的真是五花八门地层出不穷。邵飞带着我,虔诚地上敬诸神,下访民间各路大仙儿,什么花市西打磨厂换牛奶的闫瞎子,大红门外的王师傅,只要是高人谁说点什么,我们还都认真地做笔记。几乎我的速写本里的最后几页记得全是这些匪夷所思的东西。
记得是个傍晚,我们去天坛散步,发现坛上有一大群人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我们停下来,仔细地听了半天,愣是一句都没听懂,一问才知道,人家念的是宇宙语。我们当时很震惊觉得自己又落伍了,都流行宇宙语了,可我们还拚命地学什么英语?

(左图:八十年代的各路大神都开始发功了(图片来源见右下角))
终于,有一天罗导告诉我,我的剧本《白日梦》恐怕是不能进行了,因为儿影接了一部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上下集彩色宽银幕大片《少年彭德怀》。我正好赶上了电影的一个转型时代。什么都是刚刚起步:旧观念正在退场;新思维已经出现;对历史开始了重述;带有自我意识的文艺电影群体正在形成。就这样我的白日梦醒了,结束了。这事在我心里就这么放下了。我似乎没有什么失落,曾经试过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后悔!
我仍然骑着自行车满四九城地窜来窜去,什么“四月影会”,北大的三角地、“民主墙”、小剧场,这些我都去过,但我并不是参与进去,我只是到场、看热闹。参与多了以后,认识不认识的,一见面先说上一阵子艺术和人生,然后拿出各自画的画儿交流。邵飞也领着我找过著名的女画家周思聪看画,还多次拜访过王森然老先生和高莽先生。日子过得是那么的生动和澄澈,有滋有味儿。感觉周围天天都在变……。
从手提式录音机、手抄本,到午餐肉、郊外野餐;从老莫、外国电影周,到画电影票、爆炸头;从人造革皮夹克、用全国粮票换鸡蛋,到邓丽君、防震棚;从贴面舞、家庭毛片,到雅尔电子夜、天鹅湖;从皮尔卡丹时装到劳申伯个展,虽然各大单位开始有了同声传译的外国电影周,但街面电影院的《黑三角》,《神秘的大佛》,《街上流行红裙子》,也是场场爆满。虽然开始学会了化妆穿高跟鞋,我们也还在排队买带鱼换煤气罐;虽然工体空场上响起了《一无所有》的吼声,但是街上的扩音器中仍然响着苏芮的"跟着感觉走"⋯⋯

(这是我出国前最后一次和邵飞一起旅游啦,时间是1986年7月26日。)
【呼鸣油画作品欣赏】



**《油画背后的故事》锐评**
1: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回忆,因为,在接通个人历史的那一刻,一些美好的东西,就会浮现出来,让人有了麻麻的通电感受。但,可以肯定的是,心灯一定是没有亮的。真正的回忆,往往总是如此,有着长长的尖锐和痛苦。你得经过长长的暗道,然后,在开门的时候,又会出现另一个无星的黑夜,这个过程,真的漫长得有如一个世纪啊。当然,有时候,会有黎明从东山升起来,灯就亮了,似乎一切都清晰明白了,其实,这多半又是下一次继续做梦的理由吧。因为,黑白,梦魇,折腾,死亡,日子,生命,就是一个个梦的单元,交织着,纠缠着,也许,这就是我们的一生了,不是吗?
答:没事,门开着,你可以放下面具,好好地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