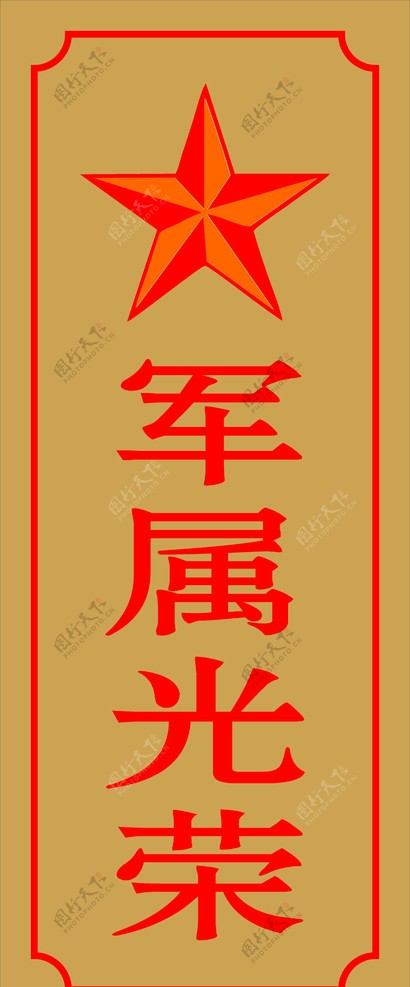
腊月廿三晌午头,暖阳热乎地照着,给这冷飕飕的天儿添了不少暖和气儿。村支书带着民兵排一群小年轻,呼啦啦地顺着咯吱咯吱响的冻土路,直奔俺家来喽。打头的小推车上,红纸鞭炮摞得老高,跟做喜庆的小山包似的,恨不能立马把新年的喜信儿喊出来。后头的人端着浆糊盆,盆沿还粘着去年 “光荣军属” 那金粉字儿,金晃晃的,像是在唠着过去的荣光。
“老卢家,那可是咱庄实打实的兵窝子!” 村支书扯着大嗓门,把春联纸抖得哗啦哗啦响,扭头冲后生们一喊:“左边贴上‘忠厚传家久’,右边配上‘诗书继世长’,横批就得是金粉亮眼的‘精忠报国’!” 话音刚落,浆糊刷子就在砖墙上麻溜地抹开了,那动静,恍惚间就跟 1978 年的番号声叠一块儿喽。俺跟恁说,当年俺大爷在舟山群岛立了三等功,可给咱老卢家长了大脸,整个村子都跟着风光。
俺家这军属的事儿,可不止大爷和叔伯们。俺俩姐姐都嫁给了当兵的,跟军旅结了不解之缘。大姐夫在西北大漠守着,二姐夫在南方海岛戍边。大姐每次收到姐夫从大漠寄来的信,那带着沙子味儿的信纸,能把她激动得直掉泪。二姐跟姐夫聚少离多,可每次通电话,眼里的念想和骄傲一点儿不少。她俩虽说地儿不一样,可都以军属的身份,默默支应着丈夫,守着小家,把咱老卢家对军人的敬重和热乎劲儿,往下传。
婶子听到动静,从灶房探出头来,手里紧攥着冒热气的糖瓜,脸笑成了朵花儿,热乎地招呼:“恁几个贴完对子别急着走,尝尝俺熬的麦芽糖!” 她这话说得,带着浓浓的山东腔,还掺着点舟山话的尾音,跟俺大爷寄回的最后一封家书一个味儿。那张舟山舰队专用的公文纸,看着庄重,二婶子眼尖,发现折痕里夹着半片禹城老家的麦叶。就这么一小片麦叶,把老远的地儿跟老家紧紧连起来,不管多远,都断不了对故土的念想。
四叔家的建军哥,自转业后,每年腊月廿五准回村。他那德州农机站的老金鹿自行车把上,总拴着截军用电话线,就像连着他的军旅日子。一进村,他就扯着嗓子喊:“建民!搬梯子来!” 兄弟俩麻溜地搭起人梯贴门神,这当口,建民哥的民兵队长袖章蹭上建军哥的农机站工装,红配蓝,跟当年他们爹的军装照一个色儿。就这么着,老一辈的军人精神,在兄弟俩身上接着传,扛起家族的荣耀和担当。
要说过年最热闹的,还得是年夜饭前放 “二踢脚”。五叔当村支书那几年,特意跑去县武装部,磨破嘴皮子要来退役信号弹壳,改造成炮仗筒,在苹果园里一杵。点火前,他脸一板,冲着北山通讯塔方向,扯着嗓子吼:“老卢家第七代军人听令 —— 放!” 这一嗓子,震得果园里退役通讯杆上的三角旗直哆嗦,旗面上褪色的 “八一” 徽标,在硝烟里时隐时现,就像讲着过去那些火热的岁月,看得人心里头热乎,满是对军人的敬重和对家族荣耀的自豪。
俺小儿在拉萨当排长那几年,每到年三十,准有穿迷彩服的小战士大老远跑来俺家拜年。小战士从挎包里小心翼翼掏出冻硬的牦牛肉,说话带着雪域高原雪粒子的冷冽:“排长让捎的,说让您包顿水饺,就当他在雪山哨所陪您守岁。” 俺婆娘一听,眼眶立马湿了,转身抄起菜刀,把肉剁得山响,那案板声,比电视机里的春晚倒计时还响,她是把对儿子的念想,都剁进饺子馅里,盼着儿子在远方能感受到家的热乎气儿。
今年,家谱匣子里又添了新荣耀 —— 小儿子的文职肩章,跟大爷那生锈却金贵的三等功章摆在一块儿。村支书来贴春联瞧见了,激动得不行,非要民兵排长把 “光荣军属” 的匾额重新刷遍金漆。刷子抹过 “属” 字最后一捺时,天上 “轰” 地炸开个双响炮,惊得梁上鸽子扑棱棱往西南飞 —— 那正是拉萨河的方向。这鸽子啊,就像带着家人的念想,飞过千山万水,捎给远在拉萨的小儿。
如今啊,时代变了,可咱老卢家这军人精神的传承不能变。在新时代,这种传承对军属群体来说,是一种坚守和慰藉。军属们守着家,让军人能安心卫国,这是小家对大家的支持。对国家国防事业来讲,它是根基,一辈又一辈军人前赴后继,靠着家族传承的精神,保家卫国。咱老卢家的故事,就是无数军属家庭的缩影,大家一起,为国家的安稳和兴旺,出着力,这家国情怀,得一直传下去,越传越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