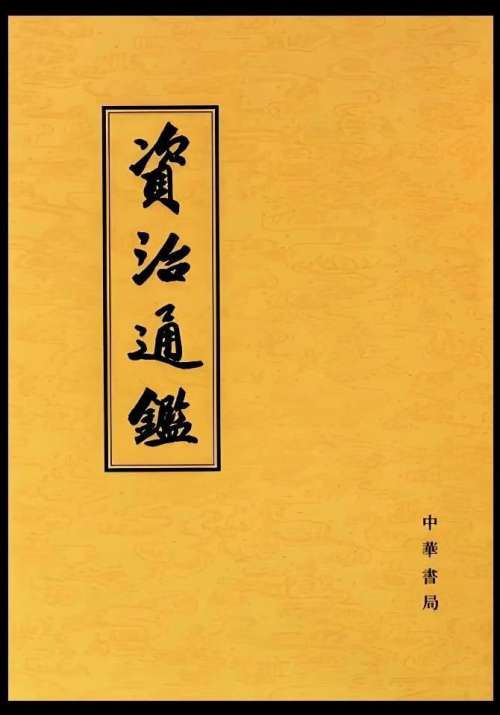
刘邦死后,朝廷发生了重大变化,吕后实际掌握了朝政。刘邦生前曾经下令,必须任用刘姓人为王,否则就要受到天下共同攻击。而在刘邦死后,吕后准备立吕氏家族的人为王,由此引起了朝廷内外的严重分歧。《资治通鉴》卷十三记载了这段历史,原文如下:
高皇后元年,冬,太后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平、太尉勃,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疌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纵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陈平、降侯曰:“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陵无以应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为帝太傅,实夺之相权。陵遂病免归。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于太后,公卿皆因而决事。太后怨赵尧为赵隐王谋,乃抵尧罪。上党守任敖尝为沛狱吏,有德于太后,乃以为御史大夫。太后又追尊其父临泗侯吕公为宣王,兄周吕令武侯泽为悼武王,欲以王诸吕为渐。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夏,四月,鲁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张偃为鲁王,谥公主曰鲁元太后。
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
太后欲王吕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恒山王;使大谒者张释风大臣。大臣乃请立悼武王长子郦侯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国。
五月,丙申,赵王宫丛台灾。
秋,桃、李华。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高皇后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87年。冬季,太后吕雉与大臣商议,打算封吕氏外戚为王,她询问右丞相王陵。王陵说:“高帝曾与群臣杀白马盟誓:‘若不是刘氏子弟而称王,天下人共同攻击他。’如今要封吕氏为王,不符合盟誓约定。”太后很不高兴,又问左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二人回答说:“高帝平定天下,分封刘氏子弟为王;如今太后临朝,代行皇帝职权,封吕氏为王,没什么不可以的。”太后听了很高兴,退朝回宫。王陵责备陈平、周勃说:“当初与高帝歃血盟誓,你们不在场吗?如今高帝驾崩,太后以女主当政,要封吕氏为王,你们一味逢迎太后意旨,违背誓约,将来有何面目去见高帝于地下?”陈平和周勃说:“现在,在朝廷上当面反驳,据理力争,我们不如您。而要保全国家,安定刘氏后代,您就不如我们了。”王陵无言以对。十一月,甲子日,太后任命王陵为皇帝的太傅,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丞相职权。王陵于是称病免职回乡。太后随即任命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任命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但审食其不负责处理朝廷政务,只负责监督宫中事务,如同郎中令。审食其向来受太后宠幸,公卿大臣都要通过他来决定政事。太后怨恨赵尧当年为赵王刘如意出谋划策,就给赵尧定下罪名。上党郡守任敖,曾做过沛县的狱吏,对太后有恩,太后就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太后又追尊自己的父亲临泗侯吕公为宣王,追尊兄长周吕令武侯吕泽为悼武王,打算以此作为封吕氏为王的开端。
春季,正月,朝廷废除了一人犯罪诛灭三族的法令和严禁妖言惑众的法令。夏季,四月,鲁元公主去世。封公主之子张偃为鲁王,赐公主谥号为鲁元太后。
辛卯日,太后封名义上的孝惠帝之子刘山为襄城侯,刘朝为轵侯,刘武为壶关侯。
太后想要封吕氏为王,就先封了名义上的孝惠帝之子刘强为淮阳王,刘不疑为恒山王。又指使大谒者张释委婉地向大臣们暗示太后的想法。于是大臣们奏请太后,封悼武王吕泽的长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划出齐国的济南郡作为吕国封地。
五月,丙申日,赵王宫中的丛台发生火灾。
秋季,桃树、李树不合时令地开花。(古人认为,异常的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是相关的,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我们阅读这段文字,看到了刘邦死后汉朝朝廷的重大变化。刘邦所坚持的用人路线受到了挑战。吕后开始任用她的家人为王,于是产生了政治利益与原则的博弈,政治人物在面对原则与利益时有不同选择。王陵坚守高帝“非刘氏不王”的原则,而陈平、周勃则从更长远的政治格局考虑,表面迎合太后,实则等待时机维护刘氏江山。这表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不能仅看眼前的立场,还需权衡各种因素,考量长远目标。太后吕雉为巩固吕氏势力,一步步突破原有政治约定,通过任命官员、封王等手段扩大权力。而大臣们有的反抗,有的妥协,反映出权力斗争中各方势力的此消彼长。这揭示了权力不会自动受到约束,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若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原有政治秩序很容易被打破。陈平、周勃看似违背与高帝的盟誓,但他们认识到在太后掌权的当下,直接对抗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他们选择隐忍,以图日后扭转局势,这体现了政治决策中的灵活性与长远眼光。在面对强大的对手或不利的局面时,暂时的妥协和变通,有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最终目标。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