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月流逝,一切都变了,但我在姥姥家成长的许多情景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今年春天,我又一次来到魂牵梦萦的于家村,寻找姥姥的老屋,寻找我印记中的老物件 ,寻找我童年的耍伴……
从我的故乡,招远市辛庄镇乔家村,到姥姥家所在的于家村,原本是有一条二华里的乡间小道,穿过我们村、五截村、于家村的庄稼地。上世纪七十年代,整大寨田,这条乡间小道永远消失了,从我们村去于家村,要么从我们村直接向北,然后从于家村西塂上沿村路进村,要么从我们村向东走二华里到五截村,再从五截向北走二华里到于家村。我选择了从乔家村向北到于家村西塂再顺路向东进村。这段路大约三华里。
进得村口,我记忆中那条铺了石块的通向村中心的北街就在脚下,但我却望而却步:这里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已是“废路”一条!我真希望见到几位熟人哪怕是生人也好探探路,可是举目四望,哪里有什么?
凭着记忆,终于摸到姥姥家住的那条过道(胡同),幸好,过道北头和南头的两座老房子还在,只是“铁将军把门”——人去屋空,而我姥姥的老屋早已不见踪影,有的只是断墙残壁,满目荒凉!
 我站在姥姥老屋的废墟前,忍不住泪流满面!这就是姥姥的老屋啊!这就是我在这生长了近十年的地方啊!姥姥,我来看您了!
我站在姥姥老屋的废墟前,忍不住泪流满面!这就是姥姥的老屋啊!这就是我在这生长了近十年的地方啊!姥姥,我来看您了!
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六十多年前……
我出生后,兄弟姊妹众多,故乡乔家村的那一间半房子根本就住不下,大约也因为我几个姨妈出门在外,姥姥一人孤身在家,所以在我两三岁时,我爹妈就把我寄养在姥姥家。因此,我从小就在姥姥家成长,直到1960年九虚岁时回乔家村念书。
童年时代的一些事情我早已忘记了,但对姥姥的记忆却非常清晰。
姥姥老家金岭镇官庄村,姓王,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嫁给我姥爷,给老于家生了三个女儿,即我大姨妈于翠美、我二姨妈于翠芬、我母亲于翠英。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姥爷因病去世,姥姥患有气管炎,常常咳嗽吐痰憋气。姥姥不识字,但会用指头掐掐算算帮丢了东西的邻居找东西,会破闷(猜谜语),会讲故事,因此在村里人缘特别好。农闲时节,她常会在过道南头的大石条上坐着给邻居们讲故事、破闷猜。她讲得故事大都是神鬼妖怪及“老皮子”、“拍花子”吃孩子、迷孩子的故事,讲得活灵活现,阴森恐怖,仿佛妖魔鬼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听得我心里一阵阵发毛,头皮发麻,晚上撤尿都不敢出门。记忆最深的是,从姥姥村到我们村,道路两旁全是庄稼地,地里还有不少可怕的、树立着石碑的大小坟头。每当我独自行走在这小路上,庄稼地里发出“沙沙”声响,不知是鬼怪还是“老皮子”,我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奓开来,脑盖似乎都要掀开来,手里紧紧攥着棍子或石块,一路跌跌撞撞跑回家。后来我断定,我从小胆子小,就是听姥姥讲鬼怪故事所致。
 至于姥姥破闷猜,那是邻居们和我最轻松开心的时候。姥姥破闷的段子很多,可惜大都不记得了,只有一段大约是这样说的:有样东西是件宝,一头有毛一头光,老爷们没有不着急,娘们没有急得慌——打一物。众人哈哈大笑!原来是“炊帚”啊,老娘们做饭缺了哪有不急的!
至于姥姥破闷猜,那是邻居们和我最轻松开心的时候。姥姥破闷的段子很多,可惜大都不记得了,只有一段大约是这样说的:有样东西是件宝,一头有毛一头光,老爷们没有不着急,娘们没有急得慌——打一物。众人哈哈大笑!原来是“炊帚”啊,老娘们做饭缺了哪有不急的!
在姥姥家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事,永远也抹不去。一是姥姥对我好极了,时时处处呵护着我。家里有了什么好吃的,她舍不得,总是先给我吃。我大姨妈在北京,常常用木箱子寄些北京点心给姥姥,姥姥总是留着给我吃;姥姥养了几只老母鸡,下了蛋,姥姥也总是用小铁勺在干柴火上炒着给我吃;那时集体分的口粮中麦子很少,普通人家常年吃不上白面馒头,姥姥就经常在铁锅里摊个“葱花饼”或者把面粉和成圆柱状在锅底下烧个“粔粔”给我吃……二是我从小受到的文学熏陶竟然幸运地是在姥姥家。姥姥不识字,家里却珍藏不少线装书和字画,这大约是姥爷留下的。我后来知道,姥爷年轻时在北京帮他大哥经商,应该是认得字的,后来因身体不好回到家乡。我记得,姥姥家的线装书,都是用书匣包装的,有《济公传》《大八义》《小八义》《三俠五义》《绿牡丹》《儿女英雄传》等。我上学识字后,就如饥似渴地读这些半文半白的小说,书中的故事和人物的确使我入迷。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线装书和书画,“文革”中我把它们当做“四旧”上交烧掉了……
我在姥姥的老屋废墟前,发呆近一个小时,眼看快晌午了,于是从过道向南街,想看看记忆中的于氏祠堂、关公庙和那口全村人吃水的水井。
这时的南街上,还是不见一人。我径直来到村西南头,找到于氏祠堂的位置,一个长满杂草的土堆进入我的眼帘——原来,我童年时于家村最好的建筑依然是废墟!前些年,我听说于家村有人牵头集资重修于氏祠堂,现在看,重修于氏祠堂还是“南柯一梦”!可叹于氏列祖列宗!
 从于氏祠堂向东不远,就是当年全村几百口人共用的水井了。 那口井水浅,常年不干且甘甜无比,用水桶打上来直接喝,从来没有人拉肚子。我可能八九岁时就学着大人的样子,用挑水的担杖上的铁钩子挂上铁水桶 ,把水桶放到水面,摆动水桶使其注满水,然后再把水桶从井里提上来,挑着回姥姥家。有时,用力不当,水桶会脱离铁钩子沉到井底。这时,年少的我并不着急,而是跑到周围邻居家,随便请个大人帮忙,用专门的打捞工具将水桶捞上来。此时,不禁想到一问题:如今,于家亲戚们还吃这眼井水吗?来到水井前,事实告诉我:这眼老井已被加盖锁上铁锁,村民早已用上了自来水。
从于氏祠堂向东不远,就是当年全村几百口人共用的水井了。 那口井水浅,常年不干且甘甜无比,用水桶打上来直接喝,从来没有人拉肚子。我可能八九岁时就学着大人的样子,用挑水的担杖上的铁钩子挂上铁水桶 ,把水桶放到水面,摆动水桶使其注满水,然后再把水桶从井里提上来,挑着回姥姥家。有时,用力不当,水桶会脱离铁钩子沉到井底。这时,年少的我并不着急,而是跑到周围邻居家,随便请个大人帮忙,用专门的打捞工具将水桶捞上来。此时,不禁想到一问题:如今,于家亲戚们还吃这眼井水吗?来到水井前,事实告诉我:这眼老井已被加盖锁上铁锁,村民早已用上了自来水。
老井东邻就是关公庙旧址了。倘徉在这里,立时想起孩提时的关公庙:坐东朝西,矗立在用石头垒起的平台上,庙内塑着关公像,左周仓手持青龙偃月刀,右关平手里也持着什么。三面墙上,则是“三英战吕布”、“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等壁画。记得那时候,常常和小伙伴们在这里说关公、讲忠义。这大概就是我的三国启蒙了。也很可惜,这座关公庙和中国人崇拜的忠义之神关公雕像也毁于“文革”。
终于,一位老者看着我在街上流连,朝我走来并招呼我:你不是锡彤吗?怎么来这了?我打量他半天,终于记起:他是我姥姥本家侄子于芳秀,按辈分,我叫他二舅。于是,我赶紧上前叫二舅,告诉他我就是想来看看于家村,看看我姥姥的老屋,看看我小时的耍伴们。二舅苦笑着:村子老了,村里人也老了,都快死了,没什么好看的了。我向他打听我儿时的耍伴:屯、石钢、聚庆、腾欣、吉顺等等,二舅告诉我:他们早就不在村里了,有的年轻时外出闯荡,有的老了投奔子女去了,现在村里有一半以上的房子无人住,六十岁以下的人很少见了。听到这些,我只有惆怅,无意再说什么了。
告别二舅返回乔家路上,二舅的话一直在耳边回荡:村子老了,人也老了,都快死了……农村向何处去?谁能告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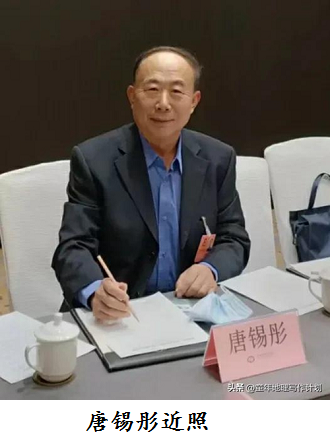
唐锡彤,1952年12月出生,1973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曾任招远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外经委主任、烟台新闻中心副主任、新华社烟台信息交流站站长、烟台国际图书文化交流中心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烟台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兼任鲁东大学教授、山东省历史学会胶东人物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委、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期关注社会问题及民国人物研究,在《人民日报》《求是》等报刊发表文章六十多篇,编著《走向世界》《伟大的工程》《吴佩孚画传》《吴佩孚研究》等著述11部,主持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一项,获省部级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发表于《求是》的理论文章《农村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荣获山东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入选作品奖。2012年被聘为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