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出生于蓬莱县医院妇产科的产房里。
母亲在县医院药房工作,自然在自己的医院里生自己的孩子。
在我快要做母亲的时候,估计是为了减轻我对生孩子的恐惧,鼓励我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母亲时常给我讲述她生我时的一个个场景。
我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母亲说我身材个头都像她,所以,生孩子的时候应该也差不多。母亲说她生孩子快,虽说是头胎,但完全没有经历一般初产妇会经历的那些。她说她上半夜觉得肚子疼要生了,就去了妇产科找值班的一位大姨(大姨是医院家属院的孩子们对父母的女同事的统称)。大姨姓李,后来做了医院领导。李大姨那天晚上值夜班,看到母亲去了,她让母亲先躺着,等她吃点桃酥,因为她有点饿了。哪知就李大姨吃桃酥的这点时间,母亲的骨缝开全了,马上就要生了。李大姨急得大叫,说我这小孩急性子,连个桃酥都不让她吃踏实了。李大姨放下桃酥赶紧来帮母亲接生,下半夜2点,我顺利来到了这个世界。
我最终果真如母亲所讲,生孩子时骨缝开得挺快,但因为女儿体重有点大,最终没能自然生产,而是紧急剖宫,用大家的话说,遭了二遍罪。
除了鼓励我,母亲还跟我说,奶奶和父亲在我出生后不久,就都回医院家属区那边的家里休息去了,妈妈和我留在医院,身边没有家里人照顾。也许是因为医院里都是妈妈的同事吧,他们才如此放心,也许是因为我是下半夜出生,他们都累了,而父亲一生都是奶奶至上,虽然算下来,奶奶在我出生时还不到50岁,父亲还是陪着奶奶回去休息了,天亮了才又回来跟医院的人一起,用担架把妈妈抬回了家。1968年的12月初,胶东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从病房到家属区,中间有好几百米的距离,路上,妈妈身上盖的被子被一阵大风吹得掀了起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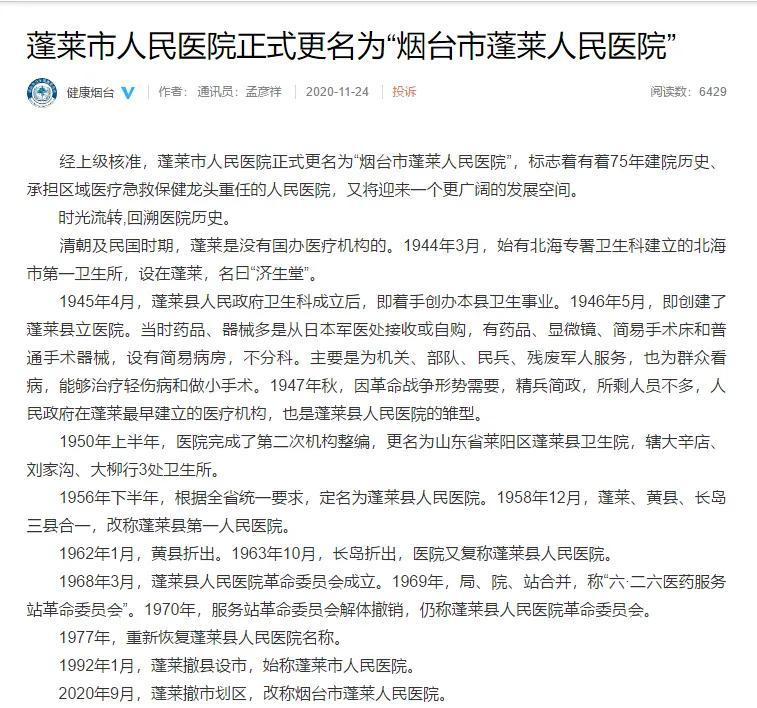 母亲告诉我,看到我是个女孩,父亲和奶奶都有些不满,父亲还说了难听的话。毫无疑问,襁褓中的我什么也听不懂,母亲如果不告诉我,我也无从知晓。其实,老辈胶东人的重男轻女家喻户晓,像我一样待遇的女孩子不在少数。后来我开着玩笑跟父亲提起我出生时他说的话,他断然否认。母亲走了快六年了,父亲怎么说的已经无从探究,当年父亲如果是一心期盼得一个儿子,看到生了个女儿口无遮拦表达失望也顺理成章。
母亲告诉我,看到我是个女孩,父亲和奶奶都有些不满,父亲还说了难听的话。毫无疑问,襁褓中的我什么也听不懂,母亲如果不告诉我,我也无从知晓。其实,老辈胶东人的重男轻女家喻户晓,像我一样待遇的女孩子不在少数。后来我开着玩笑跟父亲提起我出生时他说的话,他断然否认。母亲走了快六年了,父亲怎么说的已经无从探究,当年父亲如果是一心期盼得一个儿子,看到生了个女儿口无遮拦表达失望也顺理成章。
我的童年记忆开始得挺晚,加上从军的父亲也不怎么在家,所以,我能想起来的关于父亲的童年记忆委实不多,等到我成长为一个学习成绩优秀,家里家外不停歇地帮母亲干活的小大人后,父亲对我不像对弟弟一样动辄批评呵斥——说实话我也总是未雨绸缪让他找不到批评我的理由——但我依然很难从他身上感受到父亲对女儿的宠爱,有的只是作为长女的一份责任如影随形地鞭策着我,让我不论遇到了什么困难,都咬牙坚持,努力克服。我不记得我跟父亲撒过娇,也几乎没有肢体上的接触,比方说跟父亲牵个手,拥个抱什么的。或许,这样的父女关系,在父亲见我第一面时,便已然建立了,一生都很难改变。
母亲在我生孩子之前告诉我这样的故事,我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有时我希望母亲没有告诉我,有时我又感谢母亲告诉我实情。等到我生下自己的女儿之后,我把自己从小缺失的陪伴和关爱,都补偿在了女儿身上。所幸女儿的爸爸对她呵护备至,简直到了令我羡慕嫉妒的程度。

妇产科
言归正传。出生于蓬莱县医院的我,在医院大院度过了我的童年。那个时候,医院没有开办自己的幼儿园,我和我的同龄小伙伴们,要么有一个来自周边农村的保姆,要么老家来人帮忙照顾,要么就阶段性地被送回父母的老家由祖辈看管。等到小我三岁的弟弟出生,我也被送回招远老家住了一段时间。除了在老家待的那段时间,蓬莱县医院东西南北贯穿的几条大走廊、医院北边的大院子和东边的家属区,构成了我小学二年级之前的童年地理。
记忆中,上世纪70年代的蓬莱县医院,是三排东西向的平房,中间有一个贯穿南北的大走廊,就像汉字“王”字,将三排东西向的平房串联起来。大走廊的南门,是医院的正门,走进来,东西两侧走廊里,依次排开门诊、急诊的各个科室,应该还有打针换药的处置室、扎针烤电的理疗室等等。正中位置是个不大的门厅,门厅也分成东西两个部分,东边是什么我记不清了,应该是挂号收费的窗口吧,西边便是药房取药的窗口。取药的窗口还分两处,一处靠近南北走廊,窗比较大,是西医取药处,再往西,是另一处小窗,是中药取药处。药房轮流值班,但母亲在中药房待的时间更久,因为她学的就是中药。
南北大走廊的中部,是第二条东西方向的走廊,走廊里依次排开的是各科室的病房。妇产科的病房应该就在走廊的西头。为什么能记住妇产科的病房?不是因为我出生在这里,而是应该跟妇产科病房里弥漫的混杂着血腥味和奶腥味的复杂气味有关。更深地镶嵌在脑海中的,还有从这个走廊的西门出去后,路边的一个旱厕。
当年旱厕都长得差不多,印象中那个旱厕是个东西向的长方形,一堵隔墙将其分成东西两部分,分别为男厕和女厕。旱厕是半露天的,南边一半有屋顶,下面是水泥砌就的蹲坑和深深的便池,北边一半是两平米左右的露天地面,围着一人多高的围墙。

这样的旱厕对小孩子来说是个噩梦,我就总是担心掉进蹲坑下面的便池里。而医院家属区东墙根的那个旱厕,进入女厕的门口附近,就是整个旱厕的便池,方方正正的,敞着口,就曾经有小孩子掉进去过,那场景我没见过,但想一想就吓破了胆。
在妇产科走廊外面的那个旱厕,我除了担心不小心掉下去,还有另一种恐惧,因为在蹲坑下面的便池里,我不止一次见过不明物体,惨白的,在混杂着血迹和湿透后颜色格外鲜艳的粉色卫生纸等等内容物的便池里,这样的惨白,是我童年的一个阴影。以至于多年后,我常常恍惚,把这个场景归为我的童年幻觉,又或者我被吓坏了,本能地想屏蔽这一切。
那间旱厕,是县医院大院里我给自己划定的禁区之一,非万不得已,不会轻易走进。后来,我结识了一位曾经在妇产科做护士的大姐,熟悉了之后,跟她说起旱厕里的不明物体,说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童年幻觉。护士大姐说这不是幻觉,说早年间妇产科的旱厕,常有胎死腹中的孕妇在如厕时发生意外。我记忆中40多年前的模糊画面被大姐的话调清了焦距,我被拉回现实,尝试着去体验一个学龄前的小女孩,在血腥味屎尿味混杂的旱厕里,第一次面对这画面时的恐惧和无助。
这间旱厕,让我在童年期就见到了生的血腥。这样的生命教育在我后来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小女孩才能够克服对那份血腥的恐惧?
我想穿越到我的童年,去抱抱那个在妇产科旱厕里屏住呼吸、惶恐不已的小女孩。
太平间
 既然写到了妇产科的旱厕,那就再写一下医院西北角的太平间吧。
既然写到了妇产科的旱厕,那就再写一下医院西北角的太平间吧。
如果说妇产科的旱厕让小小的我直面了生的血腥,医院大院西北角的太平间则传递出绵绵不绝的死的悲伤,在尚不知死为何物的童年时代,就让我远远地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冷寒湿,成为我心中的头号禁区,每每还没等走近,就远远地躲了开来。
医院的北院墙西头,与太平间相距不远的位置,相应地开了一个小门,方便死者的家人从那里把太平间里的亲人抬出去,去往人生的终点站。跟着母亲在医院大院里住了近10年,没有幼儿园也没有兴趣班、学前班的童年,在医院大院里疯跑就是我的童年游戏,但西北角的小便门,我一次都没有走近过。
唯一一次在靠近太平间的大水塔附近玩耍时,我忘记了太平间的存在,忽然听见耳边传来拖腔拉调的哭声,仿佛在断断续续地诉说着什么。那是我第一次离太平间那么近,也是唯一一次。
我不敢直视,匆匆一瞥间,似乎看见一间深灰色的板式平房,大门洞开着,里面的光线像板房的颜色一样幽暗,似乎有穿着深色衣服的人影晃动,我觉得毛骨悚然,两腿发软,再也不敢多看一眼,多听一声,马上调转脚步,头也不回地跑回了东边的家属区。
工作后,因为家人多病,成为跑医院的常客。曾经,在一间建筑体量庞大的医院陪伴母亲住院,方向感一般的我,走在里面就像走迷宫一样。有一次去给母亲送检测样本,实验室是在地下某一层,我送完样本,回去时走错了路,来到了一条空荡荡的走廊,两侧墙壁上没有门,只有那种比人高的玻璃窗。
惨白的灯光下,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蓦然间,我无比清晰地联想起童年医院大院里的太平间。这家位于市中心地段的医院,没有封闭的大院,不可能有西北角的独栋太平间。或许,我在那次迷路,真的走近了位于地下某一层的太平间。我强压心中的慌乱和恐惧,故作镇定,加快脚步,按照指示牌,找到方向,快速回到了人来人往的病房。
太平间,医院的标配,在逝者去往下一站之前,供他们短暂停留,供家人整理悲伤。之前的种种,疾病和痛苦,不舍和牵绊,都在此做个了断。“驾鹤归西””“上西天”,中国人赋予死亡升仙羽化的寓意,而“西天”,是佛家所谓的极乐世界。人生的最后一次转场,在太平间,之后,乘风而去,踏歌而行,无病无灾,自由自在……如果有人把死亡做这样的解读,讲给童年的我,医院西北角的太平间,是不是会是天堂的颜色?

作者徐绍磊 留影于烟台山下海岸路
徐绍磊,毕业于山东大学。资深媒体人,高级编辑,多年从事报纸专副刊编辑工作。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