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尾随着妈,
在腾格里边上玩耍,
睡惯了泥屋土炕,
不知道天有多大。
吞冰饮雪妈不言苦,
我只管咿咿呀呀;
洗尽风尘妈仍坚劲,
我眨着眼睛一脸木讷;
妈的膝盖曾是我的扶手,
妈的肩背就是我的座驾。
因为顽劣不驯不听话,
招来老妈多少打,
遥远的童年童事,
挥之不去的童谣童话。
妈曾说过,
孕期有我是“粮荒”年景,
饿死人的事不是天天,
而是时时爆发。
妈又说过,
五七年正月十三夜雨哗哗,
她夹一粒炭火烧断我的脐带,
这个世界从此多了个男娃。
妈还不止一次地重复,
因为奄奄一息青皮瘦寡,
我在赢弱不堪中存活挣扎,
滴奶全无却有野菜糊糊,
延续了我之后的五冬六夏。
时代赐给妈一双“三寸金莲”,
可她人弱心劲儿强,
脚小志气大,
与命运抗争的不屈意志,
助她养育了一女七儿。
爹为生计异地奔波,
妈带孩儿们摸爬滚打,
拾秋荒,摆地摊,
挖野菜,捡煤渣,
在黄河边的那个小城中卫,
寻租土房遮挡风雨,
仰人鼻息寄人篱下。
为孩儿们读书几择良校,
数度搬挪那个寒酸的家,
于是现代版的“孟母三迁”,
一时间传为佳话。
儿女们成人后芝兰玉树 ,
东西南北中各显其能,
工农商学兵一样不落。
那年我长大到十八,
戎装裹身走天涯,
妈在候车室隔窗与我泪别,
如同壁虎在玻璃上爬,
那画面如雕刀刻在了我心里,
那一刻才明白了妈就是家。
之后妈是我力量的源泉,
我成了妈无尽的牵挂。
从军岁月,蹉跎困乏,
漠北边关,冰河铁马,
巴丹吉林是一流的演兵场,
我为实战淬火成钢,
学习训练争高下。
最虐心兵龄周岁那个初春,
家乡慈父病逝噩耗传,
部队一级战备命令下。
边陲坑道里弥漫着硝烟味,
儿不能灵前哭诉心里话,
一封家书失了鸿雁的浪漫,
一份电报将忠诚拷问稽查。
妈啊!边关告急!
我只能做个不孝的儿,
没有了爹爹,
您还好吗?
戎马倥偬客,
四海都是家,
走过了长天大野,
走不出那缕缕白发。
最后走到了雪域西藏,
纵使路遥水长海拔高,
也挡不住妈的声声喊话:
那布达拉宫虽然圣洁雄伟,
那雪的世界却冷的可怕,
那珠穆朗玛是地球巅峰,
尤其那缺氧听着让人惊吓。
电波里总有妈那微弱的乡音:
保重啊,我的娃!
回来吧,图个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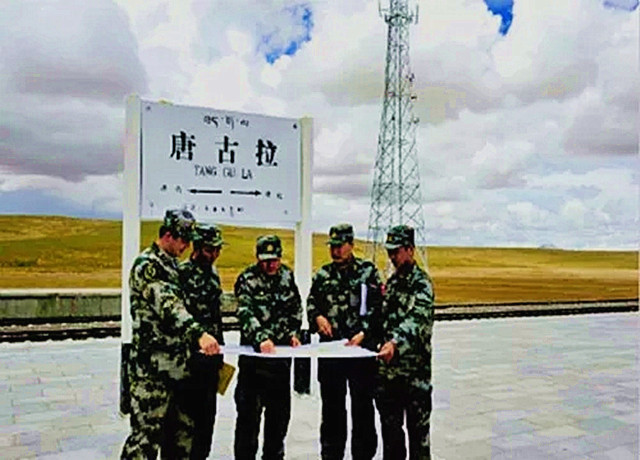
习惯了使命报国,
没去想吃苦为啥,
嚼碎委屈吞咽下,
报喜藏忧装潇洒。
蜿蜒的天路看不到尽头,
敬畏与信念却能成就神话,
世界屋脊是最好的熔炉,
能炼铁血的军阵不死的军魂,
可铸巍峨的国界碑瞭望塔,
还打造兵的傲骨意气风发。
国门卫士缺氧不缺精气神,
因为有国才有家,
一颗丹心的深底处,
永远藏着一个山一样的妈。
母亲是一种岁月,
母爱伴我完成军旅计划,
结束了青春热血的远行,
终于归乡卸甲。
都说慈母淋淋万滴血,
给我一条命的是她,
殊不知她还有簌簌千行泪,
恩德之高齐天下。
可憾子欲孝而亲不待,
我回到了久别的故土,
妈却已西天瑶池返驾。
唉!生荣殁哀一路无华,
我又成了没妈的孩子,
像荒原小草般凄怆丐寡,
梦里全是跪乳咏志的山羊,
还有泣血反哺的寒鸦。
也许灵魂的壮阔无须细节,
也许生命的养育不言伟大,
然而难忘莫过人间舐犊,
母子间的一场旷世之恋啊,
岂能轻易放下。
在高原兵的心中,
妈不是一张插图,
她是永远的珠穆朗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