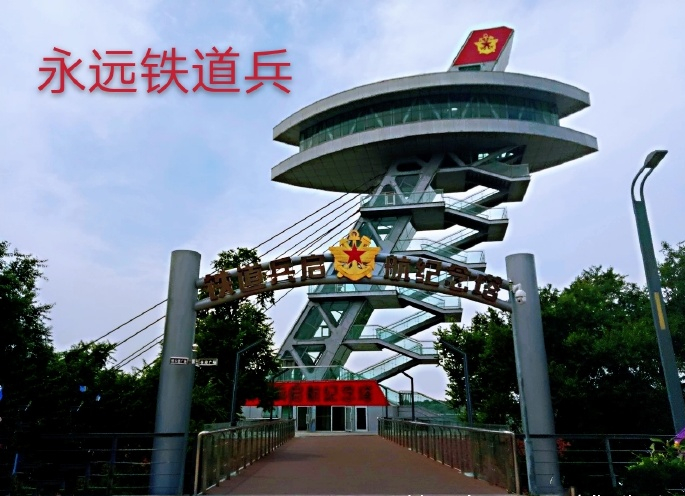
穿越大兴安岭腹地的嫩林铁路线通车了,看着锃亮的钢轨,极目远望,一排排深绿色的军用帐篷扎根在路基的边坡上,像是一片扎根森林的小屋守护着忙碌的筑路人,为他们遮风避雨,陪伴一程。
我年轻当兵时住的就是这种帐篷。军营里这种绿色帆布帐篷庄严、威武,带有刚强的气质。我们新兵住进去,觉得简朴、精致,还有几分诗情画意。在那时,它在我的心中的地位不亚于一座极品小别墅。
冬天住在林海雪原中搭起的牛毛毡帐篷中,帐篷中用汽油桶改制的炉子烧着取之不尽的兴安岭的树柈子,熊熊的火焰把汽油桶烧得泛红,冬天室外虽然是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室内却温暖如春。
当年每天超强度的劳动累得人骨头架子几乎都要散了,晚饭后坐进了绿色帐篷时,心底骤升了一丝说不清楚的满足感。夕阳下,几顶孤寂的冒着白烟的帐篷渐渐地成了我心中一道美丽的风景,它给千年沉寂的大兴安岭注入了无穷的生机和活力。这绿色的一排一排帐篷正是由于它们的简陋与孤寂,才使我们这些卫国从戎的男儿真正有了家的感觉。
在兴安原始森林和火红的达子花的映衬下,那草绿色帐篷真的是那样的威武与刚强,它就是我们当兵人天涯羁旅的绿色行宫。那绿色帐篷带有军人的气质,排列整齐的挺立在那里,可以与巍峨的大山对话,与浩瀚的大森林细语,像一个个英勇而坚强的士兵。
寒冬,祖国北疆的夜里风呼啸而来,但是刚强的帐篷顶住了这一切,它带给我们温暖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莫名的安全感。晚上睡觉时,我们先检查帐篷四周,凡有跑风漏气的地方都用“乌拉草”塞堵严实;把活动的窗户用带子系好,把门帘用一块单人床板和一根圆木顶好后才睡觉。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军营帐篷里这种别样的生活。
那一年除夕夜,战友们带上马扎聚在连部大帐棚里吃着天南地北老兵探亲归来带回的花生瓜子水果糖,讲着各自家乡过年的经历,军犬也蹲在大门口,摇着尾巴等着吃骨头……仿佛这一年所有的盼想,都凝聚在这一刻里。
吃完年夜饭饺子,全连举办了春节连队赛诗会,那年月在铁道兵部队很多人都爱写诗,这一年春节的赛诗会主题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怀念牺牲战友”。上尉老连长是40多岁的抗战军人,首先朗诵:“人民铁路我修,英雄笑傲天涯。不怕流血牺牲,丰碑人民心插!”老连长的诗句寄托着火红年代对逝去战友满满的怀念。
指导员接着:“戎马生涯踏兴安,何惧马革裹尸还。大地铁龙匍匐走,碧血丰碑美名传。”我是连部文书,即兴赋诗道:“秦时明月汉时关,古来征战几人还。卿本铁兵一小卒,酹酒英烈涕泪涟。”
刚从铁道兵学院毕业来到我们连实习的准尉技术员小马的诗很有文采:“兴安有花达子香,怒放千山送春光,责令伴我战友墓,血沃柔花变阳刚。”
1958年入伍的老班长是湖北兵,他的诗展现了夜间守卫全团粮食仓库的一段经历:”帐篷鼾声震马灯,朔风呼啸打窗棂。忽闻门板挠声响,半夜提枪打狼虫。”
炊事班长老赵围绕全连伙食写到:“化冰煮水“不留客”,(注:音译,大兴安岭盛产的一种俄罗斯大萝卜)饭热菜香充饥肠。施工常年高粱米,冻薯干笋大碗尝。”
除夕夜,刚值班下岗的新兵小王拿着纸条赶来朗诵“风过山间总留痕,莺歌婉转水弹琴。哨兵下岗不忍去,人在岭上枪挑云。”全场对他报以热烈掌声。
服役五年期满,刚探家归来的老兵一排二班长也奉上一首小诗,“新兵笑问老兵哥,说的对象中不中?臊得老兵只是笑,黑脸红成水芙蓉。”大家哄堂大笑,又是一片掌声。
炊事班小丁带着白套袖来了,先问年夜饺子香不香,大家一片赞扬“香、香!炊事班辛苦了!”小丁说俺不会写诗,俺出个谜语大家猜:“从南飞来一群鹅,噼里啪啦跳进锅,是什么?”饺子、饺子,大家又是一片欢呼。
湖北兵卫生员小谭说,俺当兵走时,对象送俺走二十里山路到县城,俺好感动,俺说四句顺口溜吧:“哥去当兵妹送行,一路缠绵一路情。挥手泪湿千里草,化作兴安映山红。”话音未落,迎来一片掌声,人们说小谭谦虚,这是多好的情诗,多好的妹子!可以给我们《铁道兵报》投稿啊!

赛诗会后紧接着是文艺演出,没有化妆,没有音响,照明的马灯也是昏暗的。石家庄籍上士给养员、我的高中同班同学是个戏迷,唱了一段《铡美案》包拯唱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炊事班长是获鹿人(今鹿泉市)用方言唱了一段“一板三吼”的石家庄老丝弦,保定兵接着来了一段保定老调,天津兵四个小伙子演了一段三句半,还有人唱歌或说笑话,小姚当兵时随时带一把口琴,即兴吹一曲口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石家庄文工团入伍,后来调到三师文工团的反派演员小贾演出一段话剧《红岩》里国民党特务头子的台词。
现在想起那歌声,仍觉得十分动听,“篱笆上开满了喇叭花,县长下乡来我家,进门来,挑水又扫地,和咱们社员是一家,和咱们社员是一家啊,是呀么——是一家!”民歌展现了那个年代党群关系、官民关系,鱼水深情,是多么融洽。
除夕之夜就这样快乐的过去了。大年初一这天,起床号还没吹响大家纷纷起床,整理内务,打扫卫生,洗脸刷牙。司号员小刘赶紧抱起一捆鞭炮,走到帐篷外的小操场上燃放起来。接着,邻近处、远处接二连三地响起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那是兄弟连队燃放的鞭炮声。整条大兴安岭深处这条千年静谧的大山沟里第一次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春节刚过,我们又要移防了。移防先要拆除帐篷。 军人的帐篷一生注定要四处漂泊,像流浪汉那样居无定所,却又没有流浪汉的自由;这就是它的宿命。这一点像我们铁道兵的生活,一顶帐篷四海为家,一双铁脚走遍天涯,我们喜欢称它为“流动的军营”。如果它不随我们去漂泊,它也就不再是军帐了。军帐如果真有生命的话,它也应像我们当兵人那样服从命令听指挥,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塞北江南,大漠戈壁,林海雪原,北极边关,四海之内都是家啊。
一段工程竣工后,一顶顶军帐被拆掉、搬走了。在铁道兵军人的心里,军帐拆掉了,昔日那种欢快的气氛就消失了,但新的欢乐又将在新工地上军帐的矗立中重现。
初春,阳光明媚的大兴安岭是那么迷人,令人陶醉。我们老兵这些年多次相约行走在美丽的大兴安岭,去根河、去乌努尔、去莫尔道嘎、去室韦、去朝阳山隧道、去图里河、伊图里河、塔河,去十八站、古林、去漠河,这里曾经是我们爬冰卧雪热火朝天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过流血牺牲的地方,这里有我们的青春芳华。
如今守候在这里的只有林业和铁路工人,只是在林区很少见到那些军绿色的帐篷了。在我们走后还有它们在默默无闻地守候着这片绿色的宝库,它们辛勤地养护着这片中国最大的枝叶繁茂的原生态原始大森林。

难忘那金秋时节,延绵的大兴安岭峰峦叠嶂,林木苍莽,景色雄奇,层林尽染,风光旖旎。高大茂密的兴安落叶松,樟子松,白桦林挺拔俊秀,郁郁葱葱,有些密林深处甚至终日不见天日,平静的界河额尔古纳河水中倒映着绵绵起伏的山林,构成中俄边界一幅多么绝妙的山水画卷。
想着这一切,我呆呆地注视着脚下大兴安岭的这片宝地突发奇想,等老了就离开繁华喧嚣,雾霾锁城的大都市,在森林边搭个帐篷,朝看旭日晨露,晚听鸟叫蛙鸣,陪着零散埋葬在山林里的战友坟茔,深呼吸着带松林清香的空气,吟一首“秋阳孤岛题诗瘦,落日平川纵马豪”的诗句,那该是怎样的一种风景!
人老了,喜欢怀旧,梦里常常忆起军帐,如若再住军帐,不知会有怎样的心境。让我想起梁实秋的散文《老年》:“时间走得说快不快,说慢不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宴会中总是有人簇拥着你登上座,你自然明白这是离入祠堂之日已不太远。上下台阶的时候常有人在你肘腋处狠狠的搀扶一把,这是提醒你,你已到达了杖乡杖国的高龄,怕你一跤跌下去,摔成好几截。黄口小儿一晃的功夫就窜高好多,在你眼前跌跌跖跖的跑来跑去,喊着阿公阿婆,这显然是在催你老”。大文豪说的多好!
老年人不再追求那花前月下的旖旎风光,但不是说老年人就一定如槁木死灰一般的枯寂。人生如游山。年轻时走进军旅,沿途有无限的赏心乐事,金戈铁马,战歌嘹亮,报国献身,兴会淋漓。也可能遇到一些挫折沮丧,歧路徬徨,不过等到日斜云暮,回望走过的山冈,却正别有一番情趣。
白居易写过一首小诗:“老眠早觉常残夜,病力先衰不待年,五欲已销诸念息,世间无境可勾牵。”话是很洒脱,未免凄凉一些。五欲指财、色、名、饮食、睡眠。五欲全销,并非易事,人生渐老总还有可留恋的在。江州司马泪湿青衫之后,不是也还未能忘情江湖于诗酒么?
我们呢,我们留恋军旅生涯、从戎岁月,那战友情深,那绿色军帐,那筑路夯歌,那除夕夜晚的诗影戏声,文艺演出,恍若昨日,将永远鲜活在我人生旅途记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