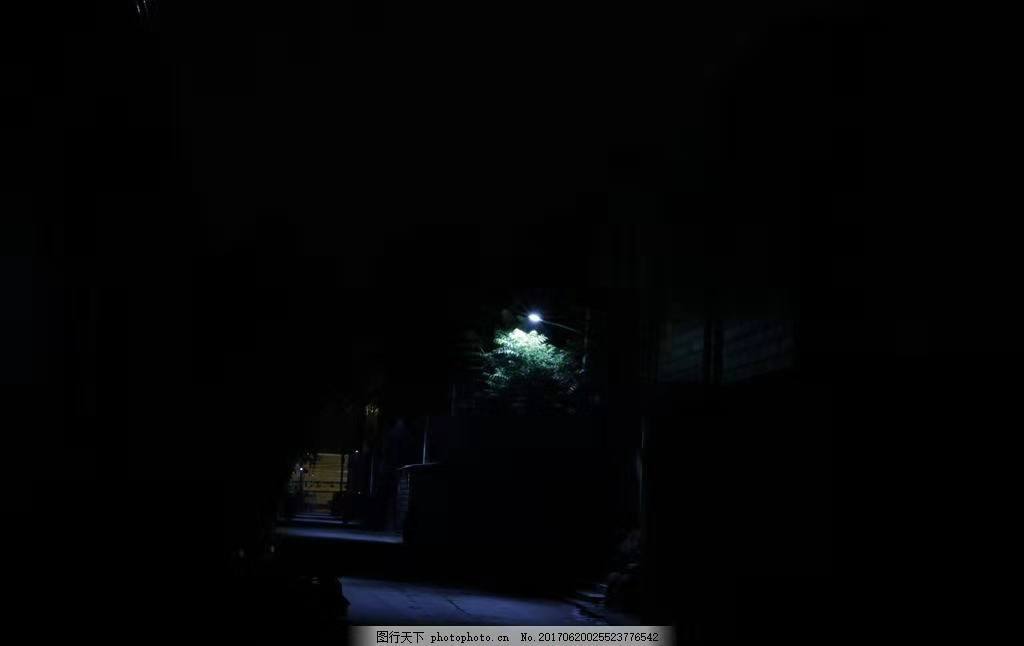
华城地区广播电台,正在播发新闻。本台记者报道:丰阳县一中一年一班海珍珠同学,荣获全省数学竞赛第一名。她天资超人,刻苦求学,各科学习成绩优异,自修英语已达到大学二年级水平。昨天下午,地委张书记接见了她,鼓励她继续努力,成为人才。
电台这条消息,立刻轰动了全地区。人们为之兴奋、羡慕。还有人展开想象的翅膀,猜度着她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颦的神童风采。
丰阳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有个“特殊”人物——孙仁,他听了这条消息,恰似心脏病突发一样的难受!
小山村叫石头洼,离县城只有五里路。村西头石崖下,有一所三间茅草房。房顶长满了蒿草,颇显孤独,房前的小园子里,长着几棵黄了叶子的葱和花拉叶子的豆角秧。屋里,箱子上尘土老厚,满地烟灰乱纸,满炕脏衣服、臭袜子。
此刻,房子的主人孙仁正对着酒杯和两个啃得囫囵半片的猪蹄子发呆。他胡子头发老长,满脸黑不溜秋。刚才传到他耳朵里的新闻,像重锤一样狠狠地击在他的心上。他低着头,闭着眼,捂着胸口,咬着嘴唇,忍受着良心皮鞭的抽打。突然,他抓起酒杯,一连干了三杯,心里难受得像火烧火燎似的。他看看这个肮脏散发着臭气的屋子,无限的惆怅迷惘。啊,珍珠,我的珍珠,我的狗眼怎么不识珍珠呢?啊,女儿,我的天仙般的女儿,是我亲手把她抛弃的呀!“天哪!”他用拳头猛力地击打着脑门,“啪啪……”他用手打着自己的心口……
孙仁年轻的时候,曾有个漂亮、贤淑的妻子。夫妻好得就像粘在一起似的。结婚正好十个月,妻子为他生下个可爱的小女儿。妻子看着爱情的果实,不知为啥哭了。不幸的事,就在哭声中发生了。
孙仁祖宗三代人稀,都是单线穿(一辈子一个男性)。到他这儿没有男孩岂不要断线绝后吗?在他爸爸看来,儿媳妇生个丫头片子,那是家门最大的不幸,有辱祖宗。老头子气得嘴斜眼歪胡子抖,大骂了孙仁一顿。孙仁看妻子生个丫头本来就大嘴巴子撅了老高,老爷子一闹腾,如火上浇油。他怨恨妻子不中用,不会生男孩,他打心眼里佩服那些一劈腿就生男孩的娘儿们,从此,他觉得妻子不随心如意了。
又是一年春草绿,妻子又分娩了,还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白生生的小脸蛋,水灵灵的大眼睛,两道眉宇间,镶着一颗似红宝石般的美人痣。可在孙仁眼里,这个小丫头片子简直是他断子绝孙的魔鬼,那颗美人痣,像苍蝇一样叫他恶心。一年来,他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啊盼,偏偏又盼来个丧门星。他恨,恨这个刚刚出世还不懂事的孩子;他骂,骂妻子是个不会生育的笨蛋。唉,队上一天工分买不了一对冰棍,孩子多了怎么养活?再说,政策不准许,这可怎么办呢……
孙仁的爸爸听说儿媳妇又生个丫头,像有人刨了他家祖坟,气得五官都挪了位置,冲儿子骂道:“你个孬种,就甘当铁杆绝后啦?把她扔了,再要个小子。”
孙仁邪火上升,决心把女儿扫地出门,一个暗淡的黎明,孙仁趁妻子熟睡之机,把刚刚满月不久的婴儿,用条被子裹起,偷偷地溜出家门。他向山里走了几步,又停下了。不,不能把孩子扔进山里,那会被狼吃掉的,她是自己的骨血。应把她扔到城边子去,或许让一个工人拣去,最好让一个条件好的人拣去,她会平安地活下去。孙仁扭头向县城走来,将孩子撂在了环城路旁,转身欲走,孩子“哇哇”地哭上了。孙仁觉得孩子在喊他“爸爸、爸爸,你不能扔掉我呀,我是你的骨肉呀……”
孙仁停住脚步,心儿颤抖啦。回身又把孩子抱起来,舍不得扔了,忽而,老爷子凶神般的面孔又出现在他的眼前,“有我在,老孙家这股人就不能断。”是呀,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还是生个儿子留条根要紧。不然,将来死后到阴曹地府,也得闹个祖宗骂,爷爷打,爸爸踢。他把孩子轻轻放下,走啦。
“哇……”寒风把孩子的凄厉哭声传送着。
他走出去不到30米远,曾在中学教过他的老师海江,像是在锻炼身体,不快不慢地跑了过来。孙仁不知是为什么,没敢和海老师打招呼,低着头,匆忙地走开。他又走出去十几米,孩子的哭声没了。回头一看,见海老师已把孩子抱在了怀里……
“啧——啧”孙仁连干了三杯酒。他两眼充满血丝,心里喷着火苗子。真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啊:“人说虎毒不吃子,可我……”他悔恨得击手打掌,嚎啕恸哭。天哪,她是我的骨肉啊,我怎么发了疯,把她扔了呢?当爸爸的良心让狗掏去了?他用拳头砸自己的脑袋,恨脑袋里装一下臭狗屎。它如果不老想着“绝后”怎么会把那样漂亮,那样聪明,将来前途不可估量的女儿遗弃呢?猝然,他看见了墙上爸爸的遗像,不禁一股怒火升腾。他用手一指,“哼”,你给我好好听着,什么传宗接代,香烟不断,屁,全是狗放屁。不叫你说这种混话,不叫你骂我,逼我,我怎么能把亲生女儿扔掉呢。你听到没有,咱那孩子全省考第一,第一呀,往后不定出息啥样呢?丫头,丫头有什么不好,有这样的好丫头,该是祖坟冒了青烟。可……可活活把宝贝当土块扔了。都是你,给你上坟填土哪,从今往后,你就等着吧……
他站起来,一把将爸爸的遗像打落在地,又踏了一只脚,镜框上的玻璃被踏得粉碎。这才转身坐下,叭!把酒杯狠狠地摔在地上,拿起一个能盛三两酒的茶杯,满满地倒上三沟特曲,“咕嘟咕嘟”地灌下了肚。他想用这烈性“家伙”把所有的神经系统麻醉,完全失去知觉。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的神经却偏偏极度的活跃起来,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痛苦地折磨着他,使他不得安宁。
孙仁把女儿扔了。一向温柔的妻子一反常态。她大哭一场,大骂孙仁一顿。便同他离了婚,带着大女儿远走高飞了。
这样一来,孙仁的名字顶风臭四十里,又过了好几年,他才好不容易搞了一个麻子脸的老婆。不过,孙仁的爸爸倒挺满意。他背地对儿子说:“别管她是麻子还是坑,能给咱爷们生个胖小子,咱烧香把她供起来,也心甘情愿。”
可惜的是,孙家爷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个麻脸女人与他结婚三四年,就是不怀孕,别说生儿子,姑娘也生不下来。孙仁的爸爸连气带急,一股火归心,上西天了。
三个月前,惟一和他说说话,解解闷的麻脸老婆竟也得了重病,没多久,也两眼一闭离开了他。
他孤独、寂寞,没一个亲人了。虽然农村实行了责任制,家家热火朝天,小日子过得跟火炭似的,可孙仁却觉得一天到晚过得没劲儿,没奔头。屋里弄得盆朝天,碗朝地,箱子、镜子上的尘土比大钱还厚;衣服油乎乎的,散发着难闻的气味。这时他更想与他离婚的老婆和带走的大女儿,更想过去甜蜜的生活。可是,人家已经嫁到了远处去了,上哪儿去寻找呢?恐怕在后半生里,再也不会见到她们了。他又想起了被他亲手扔的孩子。啊,十三年过去了,她一定长得老高老高的了吧?不知她长得像妈妈,还是像爸爸?对,想法子看看她,看一眼也是最大的满足。
星期日,孙仁忙得连饭都没顾得吃,早早地进城了。他悄然地溜进一条小街,身子靠在一根电线杆子上,双眼紧盯着几米远的一个蓝油大门。他早就打听好了,这里就是海老师的家。海老师的女儿早巳出嫁,如今家里只有老两口和海珍珠,也就是他遗弃的孩子。
孙仁望着那所严实整洁的小院子,心儿像滚油煎炸着似的。
虽然他和自己的孩子只咫尺之隔,然而见一面多么难哪!他不敢迈进小院,不敢正大光明地看孩子。他知道,自己没有那种资格,只能躲在没人的地方,躲得远远的,偷偷地看几眼。
三伏酷热,天上下火,地上冒烟。孙仁从早八点一直等到十一点,那扇蓝油大门仍是关得严严的,紧紧的。他热得全身流汗,脸被晒得火赤燎地疼,胳膊、肩膀都晒爆了皮。他还咬紧牙关挺着、挺着,双眼死死地盯着那扇大门。盼它敞开,盼着他那漂亮的“小仙女”从院子里走出来。
十二点了,那扇大门仍旧紧紧地闭着。他饿得肚子“咕咕”叫,晒得眼前金星飞溅,实在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失望地翘起脚,向院里看了一眼,把一颗恋恋不舍的心留在小院里,拖着失魂落魄的躯壳,晃晃荡荡地回家了。
孙仁的双眼像一对血泡泡,心里似被刀子剜着。他双手可劲地打着前胸,放声痛哭。他感到肝胆欲裂,心尖在流血,孩子,我的孩子呀,我不能没有你,我本来是个不孤独的人哪,为啥偏偏剩下我这一个人?怪谁?怪谁?这都怪谁?都怪你那老封建的爷爷,怪爸爸听了“老封建”的胡言……他用双手使劲地拍着桌子,恨不得把手的骨头全拍碎,恨不得当着孩子的面把这双手砍去。还有什么脸活着?让云里的闪电把我斩为两段吧,让雨中的劈雷把我击碎吧……
孙仁抓起桌上的半瓶酒,一扬脖子,一口气倒进了肚儿,用手抹抹嘴巴,腾地跳下了地。
我不能离去,要找孩子去,要告诉她,我就是她的爸爸,是她的亲爸爸。叫她狠狠地打我一顿,骂我一顿。不,我要拿着菜刀去,当着孩子的面,砍掉这一只手,砍掉一只曾扔过她的手,向她虔诚地赎罪。只要她喊我一声爸爸,哪怕只喊一声,一声,人世间一切屈辱、折磨我都能忍受下去,哪怕是死……
他把菜刀揣在怀里,喷着酒气,歪歪斜斜地冲出屋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街上走来,女儿的影子总在他的眼前飘来荡去……
又是一个星期日,孙仁依旧头顶烈日,靠在电线杆子上,望着那扇紧闭的蓝油大门。
这天更热,往马路上泼一瓢凉水,立刻冒一团白烟。晒得孙仁张着嘴喘不出气来。好容易熬到十点多钟,“吱”地一声,那扇蓝油大门总算打开了。
孙仁忙挺起身子,双眼睁得圆圆的,直勾勾地盯着大门口。他很失望,从院子里走出来一位整齐利落,挎着菜篮子的中年妇女,她回手关上门上街了。他的两眼失去了光,懒洋洋地靠在厂电线杆子上。
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孙仁忽地抖起了精神。大门口出现了一个身穿白纱连衣裙,脸蛋像晚霞一样美丽的小姑娘。啊,真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孙仁擦了擦眼,想仔细地看看,可是,小姑娘早把端着的一盆水“哗”地泼出去,一转身像朵白云托着晚霞忽忽悠悠地飘进了小院,大门又关上了。
孙仁不知是晒的还是失望的痛苦,眼一黑,身子一软,瘫坐在了电线杆子下……
从此,孙仁三天两头就到城里来转悠。顶着烈日,冒着暴雨,在那小角门的电线杆子下,在海珍珠放学回家的必经路旁,寻找着那个像晚霞一样脸蛋的小姑娘。当他看见那朵洁净的白云在自己的眼前飘过的时候,心里总是交织着一种苦、涩、酸、甜、辣的滋味……
孙仁酒气冲天,摇摇晃晃地来到街上。他站在马路旁、珍珠回家的必经之路的十字路口等着,等着他的小天使。
孩子还不到放学的时间,可是,孙仁却目不转睛地盯着,翘着脚望着,望着孩子们放学归来的方向,盼着那朵白云忽悠悠地飘过来,飘到他的眼前,飘到他的身旁。
孙仁听到了过往行人在谈论着海珍珠的事:
“大妹子,中午听广播了吗?咱县里海珍珠.全省考第一,地委书记都接见了。”
另一个更神乎其神:“听说那孩子学啥会啥,一看就会,一点就通,是个神童。”
“你看着吧,那孩子准能当科学家!”
“我看哪,长大了能当上女部长哩!”
“哎哎,说那孩子还是个弃儿?”
“是个弃儿。他爹妈瞎了狗眼啦,要是我呀,一后悔非撞死在马路上不可。”
孙仁感到心里一阵剧痛,心仿佛被一刀割去了。他觉得眼前金灯套银灯,来回飘荡。连忙双手抱住头,蹲在马路牙子上,耳朵和脑袋都“嗡嗡”叫,什么也听不见了……
残阳如血,映红了天。放学的孩子们欢快地走在马路上。
孙仁含着欲滴的泪水,站起来,在成群结队的孩子们中间,寻觅那朵心上的白云!
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像群小鸟飞过去了;路上已没有多少学生了,孙仁没有看见那朵白云,那朵托着晚霞的白云。是自己的眼睛花了,没看见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自己连眼皮都没敢眨,怎么会看不见呢?难道是她生病了,没有上学?不会的,她千万不能生病。叫我这个浑人生病,早早地死去……那么,会不会是她还在学校用功,回来晚一些呢?对了,有可能,我要等她,等她,哪怕等到明月中天,红日东升……
孙仁正在胡思乱想,突然,一朵白云托着晚霞,忽悠忽悠地飘了过来。是她,正是她,我的骨肉,我可爱的姑娘,我心灵中的小天使。雪白的连衣裙,晚霞似的脸蛋,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两道淡眉间的那颗美人痣,像颗红宝石一样闪着迷人的光。他在画上,在电影里,在生活中,从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看着,看着,白云托着晚霞在孙仁的眼前飘了过去。他来不及多想,紧走几步,一把手拉住海珍珠,含着热泪,死死地盯着她……
海珍珠一愣,望着这位素不相识,头发散乱,胡子老长;双眼似血,酒臭刺鼻的人,心里止不住狂跳着:“醉鬼,你干什么?”
“孩子,”孙仁哀求地说:“管我叫声爸爸,我就是你的亲爸爸呀?”
“啪”!珍珠挥手狠狠地打他一个嘴巴,“胡说,谁是你的女儿?”
“孩子,打吧,爸爸就是向你赎罪来的。”孙仁说着,从怀里摸出菜刀,“咔!”照自己的另一只手腕子上就是一刀,一只血淋淋的手掉在了马路上。
“啊——”海珍珠一声惊叫,拔腿就跑,一朵洁白的流云飘进了小巷深处。
孙仁望着那朵流逝的白云,过了好一阵儿才把手中的菜刀扔掉,喃喃地说:“啊,她不是我的女儿,我失去了自己的好孩子。”
夜幕降临了,路灯亮了。孙仁嘴里嘟嘟囔囔地叨咕着,叨咕着、不知去向地走着、走着,向黑暗的夜幕里走去。突然,他的心好像被什么迷住了似的,脑海里云乱雾飞,他奔跑起来,狂喊起来:“造孽呀造孽,罪过呀罪过……”他狂喊着,奔跑着,渐渐地消失在漆黑的夜幕里……




